卡拉扬说,他总是用一台 SONY 随身听录音机通过录音带来检验所灌录唱片的效果。“我从来不直接听唱片。录音带的品质总要比唱片略差,要是录音带听上去都挺好,我就知道唱片品质无可挑剔。当作完最后的修正,确认唱片已完美无暇,我就再也不听它了。除非遇上需要重录的时候。这时我就会把自己关进一间屋子独自呆上两天,反复听呀听呀,心里暗自纳闷:我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竟会是这种效果!”
“在经过精心准备的任何一场音乐会中,我已经不再听见音乐,我只是让它焕发生命而已。我自己已完全溶入其中了。每场音乐会都是一次神奇的体验,让人心醉神迷。你从自己、或者你自以为是你自己的什么东西身上游离了出来。你不再能够指挥它,它是上苍的一种恩赐。”
卡拉扬战后带领柏林第一次访美演出时,在巴尔的摩( Baltimore ),开演时仅有二十五位观众在座。卡拉扬登台了,向观众致意后,他作了难得一次的演前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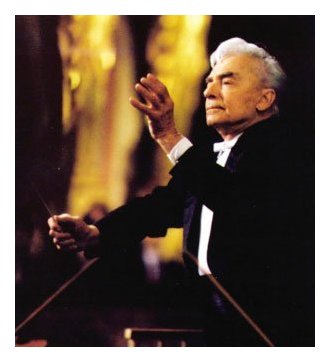
“我非常清楚,这是我指挥生涯中听众最少的一场音乐会。”他记得他自己当时是这么讲的,“听众最少,但却是最了不起的。你们不受宣传的影响来到这里,我知道你们完全是为音乐而来,我们将把一份精美绝伦的音乐奉献给你们。”
****************************************************************************************
卡拉扬年轻时在亚琛取得成功后,他又兼任了许多工作,由于繁重的工作使他的精力有些不集中。后来他偶然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关于瑜珈的书,从此便终生修炼瑜珈(后来还加上了禅宗)。
卡拉扬在跟随东京一位禅宗大师修行一段时间后,学会了集中意念。“从某种意义来讲,乐团和我在工作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于所演奏的作品,我们都把意念集中在同一个谜,即它的要旨上。每次排练我们都集中注意这个谜。我们接受它,就像天主教徒接受奇迹剧一样:‘我相信它,因为它难以理喻’。最后,当我们的注意集中到同一个焦点上时,另一种东西活起来了。我们都能感觉到它。就像乘飞机一样,是飞机让我们飞升了起来。”
“我们说‘我射击’,‘我动作’,佛语则讲‘法力使射使动’,‘法力’是我们得以仰仗的主宰万物之力。你只须驱动它,然后就任其自行发挥。当我不再念念不忘自己是在‘创造’音乐时,我便知道我所追求的效果已自然达到。”
*****************************************************************************************
卡拉扬解释指挥:“指挥真上是一种神秘的体验。进入佳境时,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做什么。我的双手已经过了三十年的训练,已从我的感觉之中独立出来了。他们会自发地挥动,音乐便如流水般滔滔涌流。能够让自己融入音乐的意韵实在是妙不可言。你的指挥完全是自然而为之,欲罢而不能,直至你完全忘记这是你的手在挥动。而与此同时,倘若哪个歌手出了错,你不会忘了予以纠正,而且是瞬间做到,无人觉察。要是某个管乐手在吹奏一个长段时,音乐进行的速度突然快了起来,那是我令他们加快的,因为我感觉出他快接不上气了,便让他吹得快一点。第二天他来对我说:‘昨天发生的事真叫我难以置信。’我回答说:‘我钻进你心中啦。我感觉到你气紧了,那个乐段眼看要不连贯了,所以加快了速度。’这就是你与演奏者之间的沟通,很难用言语解释得清楚。”
“无论我们干什么,总是学无止境的。所以我总是寻求能给我以教益的人为伍,不管是医生、科学家,还是普通朋友,只要较之我有一技之长的人都是我的老师。你知道我总是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其实只要发现谁比我强得多,我会甘作奴隶。”
*************************************************************************************
卡拉扬:“所谓歌剧,就是演员培养自己的情绪,直至强烈到非要用歌声表达不可。就像约德林一样。约德林就是纯粹的欢乐情绪的爆发。在歌剧中,就是用歌声来表达感情,表达一种特定的心境。其喜悦之情如此强烈,只有引吭高歌才足以表达。动作,如果是必要的话,也只是起到进一步强化从演员口中宣泄情感的作用。比方从欢乐变为悲伤,则不妨加点动作。演员要善于‘看’到、感受到假象的情景。在拜鲁伊特,演员唱完一首咏叹调,甚至只是一小段唱腔时,总要做一个大大的结束动作,或伸展双臂,或跺跺脚。这实在可笑。一定不能有什么‘歌剧式’的动作。”
******************************************************************************************
卡拉扬对排练的作用有一套见解。“每场排练都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进展”,他说,“指挥应懂得怎样使每一次排练取得进步。在排练结束时如果我们有所收获,心情就特别舒畅。如果尚未协调便宣告任务完成,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就会在团员中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对团员们讲:“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我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正如范·达姆所说,卡拉扬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指挥大场面(如交响乐团或剧团)所感受到的愉悦。除了中国大陆那种在体育场进行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外,没有哪种演出会像音乐会那样,有如此众多的表演者(乐团团员)听令于一个人的指挥。哪怕是较小的乐队而言,指挥都具有独裁性,那种乐团再加上合唱团多达两、三百人的演出团体就更不待言了。前面已经提到,卡拉扬的气质非常适合这种工作,而且绝大多数时候他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是有一种志得意满的心情。他情绪极好地谈及当初萨尔茨堡音乐节考虑他出任艺术总监的事。他得知有一些反对意见,有些人认为他是个独裁者。卡拉扬回答说:“他们说得不错!”
间或也会遇上一些反对意见,使他感到踌躇。一次,他在自己的圣特罗佩别墅谈论音乐时,曾对指挥家作如下定义:“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长着九颗音乐脑袋和十二条音乐家的臂膀。他是音乐的使者,是音乐界的祭司,是和平与美的使者。千万人崇拜他,其余的人则谴责他是独裁者、无耻地以音乐谋取权利,一个骗子。历史上曾有哪种职业,像指挥家这样受过如此截然相反的对待?惟有宗教主义的盲目狂热能与之相比。”
“这是艺术创造的一种独特的体制:一个人被赋予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总管一切,包括演员、歌手、预算、计划和节目。别的任何领域里哪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几乎别的所有行业里,领导也得受制于人,诸如委员会、董事会、监察员、工会等,都有权使事情受到控制。一个人受到如此信赖,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是最后一遭了。当然,这种领导原则也有其弱点。希特勒不是自称为‘元首’吗?所以这个词也有招人讨厌的一面。这是个令人生疑的词。当人们意识到某人要按他的遗志行事时,他们就常会变得多疑。领袖——独裁。如今,表达自我的强烈意愿往往容易招致批评。人们似乎不敢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并靠自己的实力去实现它。但在纯艺术领域这种原则是有价值的。必须有一个人表达意见,否则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之作产生。”
为艺术尽心竭力和“一人掌权,一人说了算”的哲学是卡拉扬班子的核心。
*****************************************************************************************
卡拉扬一贯宣称对自己指挥生涯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托斯卡尼尼,另一个是富特万格勒。 1963 年,卡拉扬说:“作为指挥家而让乐团和自己共同担负阐释音乐的责任,富特万格勒是第一人……虽然我从未打算改变这种风格,但我还是试图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精确性的要求,托斯卡尼尼正是凭着自己的绝对控制力把这种要求加诸乐团的。”
卡拉扬与托斯卡尼尼初次接触时才 15 岁,他说:“托斯卡尼尼在斯卡拉干了 8 年,这是他最辉煌的时期。但他离开时总经理却暗自庆幸。有一回他指挥排练《唐乔瓦尼》整整排了三个月,彩排都过了他却突然撒手不干了,说‘这戏没法上’。不过对我来说,他却像月亮一样高不可攀。他是个巨人。据我所知在唱片灌录上他也算是开山鼻祖。我跟他相识是在拜鲁伊特(当时我在乌尔姆工作)。他正指挥演出《唐豪瑟》。演出之完美令我惊叹。在当时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回到乌尔姆,作为新演出季的开场我也指挥了《唐豪瑟》。站在乐团面前,我脑海里回响着托斯卡尼尼指挥出来的音乐。”
“托斯卡尼尼致力于追求乐音的完美,追求表达的精确。富特万格勒则在各方面都跟托斯卡尼尼截然相反。托斯卡尼尼非常严格,富特万格勒却非常自由。富特万格勒指挥歌剧并不出色,他从来就不具备统帅歌剧演出的技艺。但他指挥古典时期音乐的才能却非常杰出。指挥古典时期交响作品他是最棒的。他善于让乐团与自己之间达到相互沟通,从而使双方共同投入音乐创造之中。托斯卡尼尼是个独裁者,要是他在指挥中表现欠佳,他会责怪听众没有进入状态。瓦尔特·列格曾说,在托斯卡尼尼指挥下,任何作品听上去都仿佛是罗西尼写的。托斯卡尼尼的知识从何而来?来自地方上的乐队中午在街头广场的演奏。那类演奏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最深刻的。我很幸运,从小听的都是高水准的演奏。托斯卡尼尼从未真正了解贝多芬的作品。他指挥《第九交响曲》不失正确,但却是蛮横的,某种东西给失却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还是咬牙搏斗到底。”
卡拉扬最爱讲富特万格勒的一个笑话是:“一次富特万格勒演出迟到了,他一边急急忙忙地冲进音乐厅,一边问深情愕然的引座员:‘他们都开始了么?’”
卡拉扬说:“富特万格勒最爱用的一个词是 jein (德文缩略词,肯定和否定之义兼而有之),因为他总是拿不定主意。我接手柏林爱乐后,一位原先跟富特万格勒共事的首席小提琴手曾跟我讲起过富特万格勒指挥的一次演出。当交响曲奏到一处节奏缓慢的过门时,富特万格勒目光忧愁地望着这位首席小提琴手,因为他讨厌给示意继续的手势。于是这位小提琴手便径自奏了下去,他说当时富特万格勒的眼神看上去如释重负。他不愿意音乐太过清晰,惟恐失去了想像的余地。他要求的音乐非得如雾中看花,迷离朦胧不可。”
“有人问过柏林爱乐一位团员,在富特万格勒手下演奏,他们怎么知道当于何时开始?那人回答说这很简单,只要看见富特万格勒在台侧一露面,团员们便默数节拍,数到第四十拍便只管开始。”
***************************************************************************************
卡拉扬说,他总是用一台 SONY 随身听录音机通过录音带来检验所灌录唱片的效果。“我从来不直接听唱片。录音带的品质总要比唱片略差,要是录音带听上去都挺好,我就知道唱片品质无可挑剔。当作完最后的修正,确认唱片已完美无暇,我就再也不听它了。除非遇上需要重录的时候。这时我就会把自己关进一间屋子独自呆上两天,反复听呀听呀,心里暗自纳闷:我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竟会是这种效果!”
**************************************************************************************
通过观察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出《德意志安魂曲》,你会感到“指挥家”这一本就难以定义的角色更多了一层谜一样的色彩。它还是我想到了早些时候卡拉扬所讲的一段话。大多数人认为,“作曲者怎么写就怎么指挥”是托斯卡尼尼的特点,我们当时的话题就是由此开始的。“我有一位了不起的朋友,维克多·德·萨巴塔(也是马泽尔的老师),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指挥家,”卡拉扬说,“我在斯卡拉歌剧院时,他常来听排练。那次我正排练《唐豪瑟》,到一个合唱段我让乐团继续演奏,因为我想去后面听听效果,维克多当时正坐在厅里,他做了一个非常优雅的手势,上台接替我继续指挥。瓦尔特·列格也在场,后来他告诉我说,那是一次最为有趣的体验。维克多无疑是位伟大的指挥家,从他接过指挥棒那一刹那,音乐就起了变化。而他并未说片言只语,全凭他展示在乐团面前的个性特征。音乐的整个特质都变了。姑不论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这无关紧要;反正是截然不同了。”
“我说我现在明白个性影响的含义了。当然,因为他指挥那个乐团已达 25 年之久,已形成他自己的总体音乐风格,所有音符的组合无不打上他的风格的烙印。所以他一接过指挥棒,团员们抬眼一瞟,便自动按照他的指挥风格演奏起来。从那以后我总讲,讨论何为音乐真谛是没有什么用的。既然我们信任某人让他指挥某个作品,我们就必须理解他是在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指挥。”
“歌德的《浮士德》中谈到时代精神,即某一特定时代之精神。在现实中,这其实是人们的精神,他们从中(就象在镜子中一样)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时代。精神时代——时代精神,意既一切都在我们的思索之中回溯再现。在音乐中这是个重要词语。我不能让我自己分心。音乐于我就是一切,我已经全身心地溶入其中了。”
卡拉扬重视科学,但他说音乐并非一门科学。“曲谱只是提供给我们暗示,我可以用同样的速度演奏同一首曲子,一遍显得仓促,而加一遍却恰到好处。巴托克是个讲究精确的人。在写《管弦乐协奏曲》时,为确切地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他以秒为单位在谱上标明了时速,例如从某处到某处需 35 秒。有一次,我指挥一些学生将这部协奏曲的一个乐段演奏了两遍。我处理时全作了改动,但两遍演奏下来不多不少刚好是 35 秒。有人说托斯卡尼尼是对的,因为他完全是按照作曲者所写的指挥。这简直是胡说。”
“音乐有他自己的呼吸。歌德有首诗讲到呼与吸的对比。吸气给你压力,呼气则使你放松。诗中说,生命多美妙,它是呼与吸的混合;感谢上帝,它让我们感到压力,又让我们得到解脱。瑜珈功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就立足于气息吐纳的节律变化。至于音乐,它就如潮水,有着自然的涨与落。谁要是把握不好速度,那我是无法忍受的。遇上这种情形我会变得让人受不了。我生来就讲究自然节奏。为更准确,我甚至借用节拍器。我在西德多特蒙德的马克斯·勃兰克学院做过一个实验。先选定任意一个速度,比如说每分钟 86 拍。然后在钢琴上先后用四分音符、三连音、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各奏一遍,末了再回头用四分音符弹奏,看看是否仍保持原先的速度。现在,每个乐团都做这个测试,结果奏到十六分音符时都比原定速度快了百分之十至二十。要经受住这个检测是很难的,错误率可以高达百分之三十,而我只快了百分之二。他们都说我脑袋里肯定装了一台电脑。”
“海森堡是德国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提出一个理论:就是‘研究’这一行动本身就会使你的研究对象,比如原子、分子发生变形。譬如你要研究一团雪,于是你将它握在手中,而就在此刻你手掌的热能业以使它发生了变化。同理,你掌握了一个乐曲,再把它交给乐团,在这些行为过程中它也会发生变化。一个人除非同意这一观点,否则他就欣赏不了音乐。”
“就连乐谱印刷版本的不同也会使音乐发生变异。有些演奏者总是使用最老的版本。我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分辨上面的音符的。有时他们也会抱怨。有一个例子,维也纳爱乐的团员们抱怨一些老乐谱看不清楚,我便给他们换了新版本。新谱印刷精美,非常清晰。结果,因为新谱给予他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觉印象,团员们完全茫然了,连每次演奏的停顿都变了。我对他们说:‘别忘了你们已依据旧谱演奏了许多年。你们的祖辈、父辈都用过它。你们曾依据它表达过你们的所有希望、绝望和你们的爱。这一切都寄托在那谱上,你感觉到的是一个丰满而完整的形象。而现在,你们第一次面对这黑白分明的新谱时,这一切便都荡然无存了。”
“一次在排练一部贝多芬作品时,每次奏到某一个地方时速度就变快了。于是我让他们把乐谱给我瞧瞧。原来排印时为便于分段,有几个音符挤着排在这一页的末尾。原来问题就出在这小小的视觉上。印刷效果使音乐效果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